“男同”HIV感染者的 秘密家園
他們在“嶺南夥伴”逐漸走出陰霾
2014-11-26 金羊網集團 新快報 記者/劉子珩、郭曉燕 報導
在愛滋病的傳播管道裡,性傳播已遠遠超過血液傳播,成為主要的傳播途徑,其中男男同性傳播比例快速上升。廣州疾控中心2013年6月的資料顯示,“男同”(男性同性戀者)性行為人群HIV感染率已經達到10.94%,即不到10個人中就有1人“中招”。
從2008年開始,廣州市疾控中心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對這一傳播模式進行高危干預。將愛滋病檢測點設置在公益組織所在地的社區,並購買他們的服務,為特殊人群提供檢測、心理危機干預等成為一種合作方式。
設在天河繁華商圈內的一座商住樓內的“嶺南夥伴”就是廣州市疾控中心選擇合作的其中一個公益機構。933名男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從嶺南夥伴的工作人員口中得知了他們的患病消息。其中,最小年齡感染者,16歲,青蔥一般的年紀;最大年齡的感染者,則超過70歲。
辦公室是嶺南夥伴與廣州市疾控合作的檢測中心,裡面有一張舒服的軟沙發,一個魚缸,放著輕音樂,他們儘量讓每天登門的幾十名“男同”不感到拘謹。他們希望這裡能成為“男同”愛滋病感染者的秘密花園,幫助他們走出陰霾。
但作為專為“男同”提供愛滋病檢測和諮詢的諮詢員,李小米遇到了數不清的“健康”諮詢,光是在微信上,就為此添加了200多個好友。
阿成就是其中一個,他說自己並不是同性戀,只是有一次被朋友帶去了男同的澡堂洗澡,卻不想跌了一跤,流了血。他自此惶惶不可終日,“我會不會因此感染上愛滋病?”
李小米哭笑不得,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頓,可是在阿成的堅持下,還是為他做了檢測,顯然,他沒有感染。
“他對愛滋病的瞭解太少,這類恐懼根本沒有必要。‘恐愛’是因為宣傳教育的滯後而產生了錯誤觀念。”李小米的工作就是不斷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高危群體,只有高危行為,以為自己安全的人最危險。”
只是工作時間越長,李小米發現了越多問題,公眾對愛滋病的偏見依然存在,甚至是患了病的人本身,也沒有對愛滋病完全瞭解。他們需要被普及知識,並且得到心理與生理的健康諮詢。
從耽美小說到“男同”網站
李小米,目前是國內男同組織裡的唯一女性負責人。她說自己從高中開始關注“男同”現象,起初只是因為“好玩”。
高中時,她從同學那借了一本臺灣言情小說,發現,原來兩個主角都是男的。這讓她震驚,感到莫名其妙。她上網查找,這才發現,這是一個現實存在的,並且有相當規模的人群。而這類小說,通常有一個詞彙歸納,叫做“耽美”。這是一個出自日本的詞彙,被引申為了男同性戀文化。
直到進入大學,李小米開始在生活裡認識到朋友,他們用紀實文學的手法表現“男同”的生活,這與耽美又是大不同。
少了浪漫的幻想,多了殘酷的現實。真實的“男同”世界,絕不是耽美小說裡的那麼美好。李小米開始注意廣同網——這是一家總部在廣州的同志網站,在當年,它的頁面風格和內容品質就很出眾。
大學時,李小米結識了廣同網的負責人。同年,她成為廣同網的文學版版主,後來去到網站辦公室成了一名秘書,這算是真正地進入了中國“男同”的圈子。
那時的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遠不如今天,大家不瞭解,且存在歧視。廣同網,側重的是社區建設,讓網站上的人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究竟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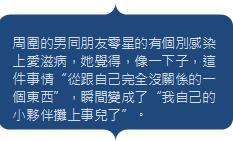 後來李小米來到了廣州,廣同網與清華大學合作,第一次在互聯網上針對“男同”群體進行了大規模的橫斷面調查。調研發現:“男同”群體的知行分離是一個突出問題,愛滋病基本知識知曉率很高,但安全套使用率持續偏低。
後來李小米來到了廣州,廣同網與清華大學合作,第一次在互聯網上針對“男同”群體進行了大規模的橫斷面調查。調研發現:“男同”群體的知行分離是一個突出問題,愛滋病基本知識知曉率很高,但安全套使用率持續偏低。
那個時候,李小米發現,周圍的男同朋友零星的有個別感染上愛滋病,她覺得,好像一下子,這件事情“從跟自己完全沒關係的一個東西”,瞬間變成了“我自己的小夥伴攤上事兒了”。那時她有一個強烈的感覺,“雖然還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但是恐怕得開始做了。”
“學校宣傳畫中沒有一個是正常的”
2007年10月15日,李小米和廣同網的另兩位核心成員,發起成立了嶺南夥伴社區支持中心,作為廣同網的旗下機構。2008年開始與廣州市疾控中心合作,開展為“男同”提供艾滋檢測和諮詢。2011年至今,又開始與市疾控中心合作運營專門面向“男同”的檢測中心。
自此,嶺南夥伴成為了廣州市疾控中心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為特殊人群提供檢測、心理危機干預等的防艾機構之一。疾控中心認為這些組織更容易接觸到目標人群和敏感人群,同時也更容易獲得認可和接受。
“在男同圈子裡,有30%的人,認定了醫院、CDC(疾控中心)的醫務人員更專業,他們願意去到那裡做檢測。而70%的,則寧願到像嶺南夥伴這樣的組織來進行心理諮詢,做檢查,這裡讓他們更安心。
”
7年來,嶺南夥伴為“男同”提供了2.1萬多次檢測資料。不過這期間也並非一直順風順水,各種磨合也曾給秘密花園帶來各種波折。
第一次的波折是“逼遷”危機。2008年8月15日,嶺南夥伴找到了最早的辦公地點,在越秀區一個住宅社區裡。不想後來被人寫了匿名公開信,塞進了每個社區住戶的郵箱,說這是一個同性戀愛滋病組織,聚眾淫亂,呼籲社區居民抵制,居委會、街道辦等取締。
嶺南夥伴最終請來了廣州市疾控中心的醫生,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科普”,總算渡過了一次難關。
而後因為房東收房的關係,又搬了兩次,才來到了現在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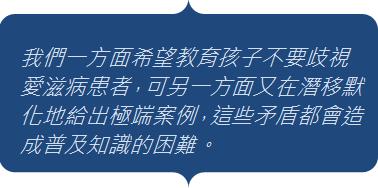 但是李小米從這次事件中看出,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歧視與畏懼其實仍然存在。“相當程度上源於對它的瞭解過少”,李小米與嶺南夥伴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普及相關知識。他們到學校演講,發現現在的青少年其實有不少疑問,每回都有學生事後加她的微信。
但是李小米從這次事件中看出,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歧視與畏懼其實仍然存在。“相當程度上源於對它的瞭解過少”,李小米與嶺南夥伴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普及相關知識。他們到學校演講,發現現在的青少年其實有不少疑問,每回都有學生事後加她的微信。
還有一次李小米在學校的宣傳畫上,看到有一版叫做“愛滋病的部分表現”,上面全是恐怖圖片,“渾身都是腐爛的肉,甚至長了白泡的生殖器,總之,沒有一幅是正常的,我們一方面希望教育孩子不要歧視愛滋病患者,可另一方面又在潛移默化地給出極端案例,這些矛盾都會造成普及知識的困難。”
還有一次波折則是醫護人員最擔心的職業暴露問題。
那是2011年的12月,市疾控中心的一次檢測時,一位檢測者因為抽血不順利,僅僅在針頭上留下了血液。護士想幫他,就直接拿著針頭去做檢測了。不料和李小米迎面撞上,一針紮在了她手上,又彈開了。
李小米至今記得,雖然只是一個小針孔,但血從來沒有那麼踴躍地往外冒過。護士和她都蒙了,趕緊給做緊急處理,擠血、消毒。針頭中殘存的血液快速檢測的結果出來,試劑顯示兩條紅線,初步懷疑檢測者感染了愛滋病病毒。護士又急,再擠了一次血。
為了防止感染上愛滋病,李小米開始服用緊急阻斷藥物。對於初期服用者來說,愛滋病藥物具有很大的短期副作用,她開始頭暈無力,像喝醉酒一樣,並且在每天上午很規律地20分鐘吐一次。
不過還好,短期副作用幾周時間就會自然消退,在緊急阻斷藥物連吃了28天之後的三個月和六個月時間,她又分別做了兩次檢測,都是陰性,證實自己沒有被感染,也就停了藥。之後,所有諮詢員被禁止接近抽血台和快檢試驗台。
這段經歷讓李小米意識到,與普通公眾不同,醫務人員對愛滋病和感染者的恐懼與排斥,不一定是因為無知,而更多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憂慮。這使得嶺南夥伴在開展基層醫務人員反歧視培訓時,更多基於“普通人vs普通人”的立場切入。
哭的是少數,大多數人第一反應是蒙
到了今天,雖然行事低調,但是“嶺南夥伴”在“男同”領域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每年在廣東省,嶺南夥伴大約要做8000人次的愛滋病檢測。如何面對剛剛得知自己患病的人,這需要知識、技巧和經驗。
即使幾次搬家,開放第一天,需要幫助的人仍能順利找到新址。 李小米也從接觸第一個男同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緊張激動,變為今天能從容當好一個傾聽者。
她至今還記得第一個由她跟進並確診的服務物件,一來就不停地哭。在沒聊幾句後,邀請她去家裡吃飯。這其實是對“嶺南夥伴”的測試,看他們是不是真的想要幫助自己。但李小米拒絕了,“他要是請我去外面吃,我一定會去,但是到一個陌生男人家裡吃飯,太曖昧了。”雖然如此,以後的交往中,他們還是形成了相互的信任,“我對感染者所有的理解和態度,都來自於我所接觸的每個感染者本身”。
 來這裡的人,或單刀赴會,或成雙成對。起初有說有笑的,進來後一下子沉默了下來。填表、抽血,等那張沾染血滴的試紙上出現醒目的槓槓:一道槓槓,陰性;兩道,陽性。在這個群體裡,極度恐愛,害怕得病的是少數;抱著必死的心態,中不中無所謂也是少數;中間的群體,對疾病本身或多或少有一種恐懼。
來這裡的人,或單刀赴會,或成雙成對。起初有說有笑的,進來後一下子沉默了下來。填表、抽血,等那張沾染血滴的試紙上出現醒目的槓槓:一道槓槓,陰性;兩道,陽性。在這個群體裡,極度恐愛,害怕得病的是少數;抱著必死的心態,中不中無所謂也是少數;中間的群體,對疾病本身或多或少有一種恐懼。
所以,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都不會大哭,“大哭四小時的那種算是新聞了,大部分人都是蒙。”李小米說,這種蒙就是整個呆住了,手開始微微地顫抖。
在一堆他可以想起來的問題裡抓,“我還能活多久?”是所有人關心的第一個問題,但大多數人很快意識到可能這個病沒有那麼容易死,不過接下來該怎麼辦?很多人這時會“十萬個為什麼”上身,拋出一系列關於這個病無巨細的問題,“能不能治”、“怎麼治”、“治療要花多少錢”、“手術會不會被拒診”、“單位會不會發現”……但每每回答到一半,他們就會打斷,然後冒出新的問題。這意味著,這些可能都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等慢慢清醒過來後,他們才會開始問想知道的問題,“我還要考公務員入職體檢怎麼辦”、“我馬上要度假了,還能去嗎”……其中最複雜的一個問題是“我應該告訴家裡人嗎?”
要不要告訴別人
曾有一個學生將病情告訴了自己最好的室友,但之後室友再沒有和他說過話;也有人告訴了家裡,家人表面上接受了,背地裡卻以淚洗面。
“你告訴他們的原因是什麼?”李小米通常會這樣反問諮詢者,“如果對方對愛滋病不能接受,甚至恐愛,就只能選擇不說了。”
隨之而來的問題還有,“我該說出真正的感染原因嗎?”一個男同愛滋病毒感染者在和家人解釋為何感染上愛滋病的時候,稱自己是在小診所打針感染上的。這在李小米看來是一個拙劣的謊言,基本等於告訴別人自己是在撒謊。
事實上,以當今醫療技術,愛滋病雖然不可被徹底治癒,但是治療妥當,還是可控的,這就像糖尿病一樣,雖然不可根治,但可以靠吃藥維持自身的健康水準。“愛滋病是慢性病,可以有效預防和治療,嚇死的比病死的多。”李小米從工作經驗中總結,“早期發現很重要,不作死就不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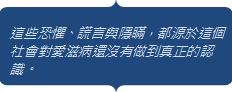 但是吃藥必須要遵守相當嚴格的控制,每天都必須按時吃藥,不然藥效就會大打折扣。李小米接觸過一個愛滋病患者,因為必須要遵守10點吃藥的要求,有一回他當著男朋友的面吃了。愛滋病的藥與其他藥物外觀上有明顯的差別,就像維生素片一樣。男友問他是什麼藥時,他閃爍其詞,本以為可以糊弄過去。不料對方卻是個細心的人,最終在衣櫃裡找到了裝藥的瓶子,並按著藥丸上刻著的英文縮寫,在網上搜出了真相。
但是吃藥必須要遵守相當嚴格的控制,每天都必須按時吃藥,不然藥效就會大打折扣。李小米接觸過一個愛滋病患者,因為必須要遵守10點吃藥的要求,有一回他當著男朋友的面吃了。愛滋病的藥與其他藥物外觀上有明顯的差別,就像維生素片一樣。男友問他是什麼藥時,他閃爍其詞,本以為可以糊弄過去。不料對方卻是個細心的人,最終在衣櫃裡找到了裝藥的瓶子,並按著藥丸上刻著的英文縮寫,在網上搜出了真相。
這些恐懼、謊言與隱瞞,都源於這個社會對愛滋病還沒有做到真正的認識。
李小米理解這群人的苦惱,她作為服務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相關工作者,也沒有如實將工作告訴母親。大學時她曾提過一次在做的事,母親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她便索性說自己在英語培訓學校做諮詢工作。後來也曾試探過一次,說自己想辭職,去一家性健康的機構,母親還是接受不了。“所以在媽媽去世之前,我在這裡只能叫李小米。”
小唐也沒有對家人說起自己的工作,他是嶺南夥伴與廣州市疾控中心合作的檢測中心的員工,主要工作是抽血,理論上來說是風險最大的。
小唐來這裡開始純屬偶然,畢業之際,他的一位朋友剛好從嶺南夥伴辭職,便告訴他,“有一份好工作”可以介紹。沒有細說,小唐到了辦公室才知道,工作的機構是什麼。
不過他還是接受了,他本就想做個社區醫生,留在廣州是第一選擇。他憑藉自己的醫學知識覺得,按流程正規操作,不會出現問題。
李小米和嶺南夥伴要做的還很多。“只能說,仍需努力。前段時間我為‘男同’發放安全套,這是他們最重要的保護工具,但是用不用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隱私原因及受訪者要求,文中所有名字均為化名)
新聞出處: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4-11/26/content_588905.htm?div=-1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4-11/26/content_588911.htm?div=-1…





 愛滋藥物副作用 皮疹最受感染者困擾
愛滋藥物副作用 皮疹最受感染者困擾 惡化、影響身體健康的風險之中。」
惡化、影響身體健康的風險之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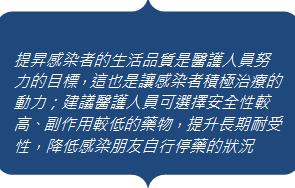 對此,台灣愛滋病學會常務理事、台灣露德協會理事王永衛醫師表示:「從診療時間即可發現,醫療人員在與感染者溝通上投注許多心力;所以,只要雙方有充分的討論,副作用是可以了解與改善的。提昇感染者的生活品質是醫護人員努力的目標,這也是讓感染者積極治療的動力;從社會公衛角度而言,只要協助感染朋友穩定控制,也進一步降低疾病傳染風險。所以建議醫護人員可選擇安全性較高、副作用較低的藥物,提升長期耐受性,降低感染朋友自行停藥的狀況;目前抗病毒藥物皆有不錯的病毒控制成效,近期固定劑量組合抗病毒藥物在方便性、有效性及副作用上也已經有顯著改善,更能維持感染者的生活品質。」
對此,台灣愛滋病學會常務理事、台灣露德協會理事王永衛醫師表示:「從診療時間即可發現,醫療人員在與感染者溝通上投注許多心力;所以,只要雙方有充分的討論,副作用是可以了解與改善的。提昇感染者的生活品質是醫護人員努力的目標,這也是讓感染者積極治療的動力;從社會公衛角度而言,只要協助感染朋友穩定控制,也進一步降低疾病傳染風險。所以建議醫護人員可選擇安全性較高、副作用較低的藥物,提升長期耐受性,降低感染朋友自行停藥的狀況;目前抗病毒藥物皆有不錯的病毒控制成效,近期固定劑量組合抗病毒藥物在方便性、有效性及副作用上也已經有顯著改善,更能維持感染者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