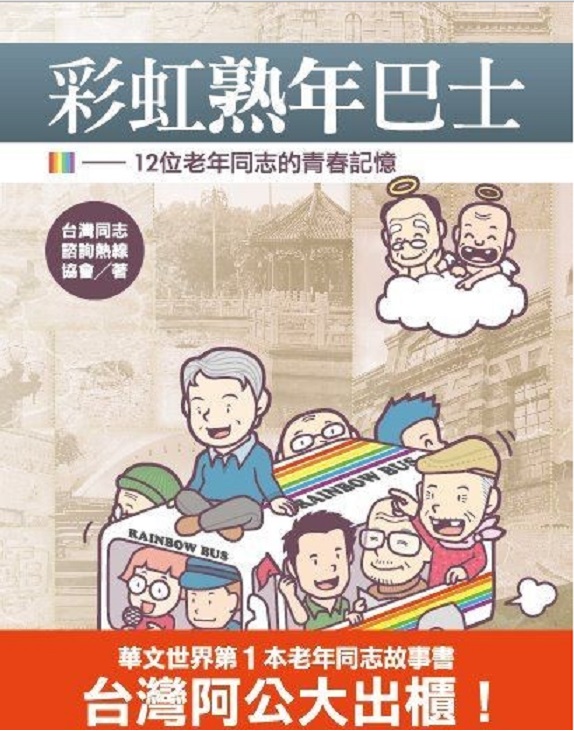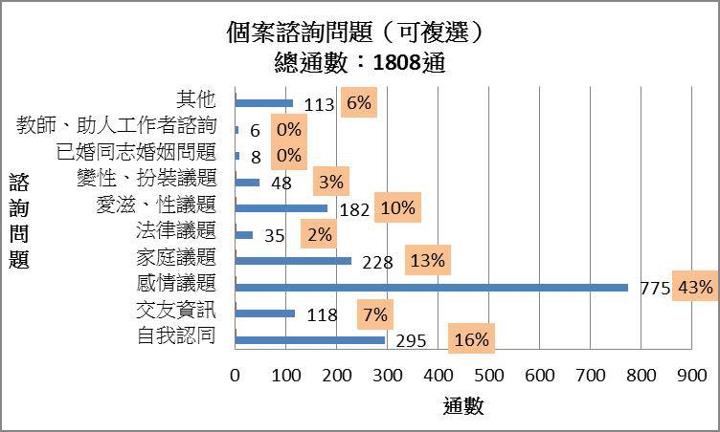【爽歪歪網站推薦】
本文細數了台灣過去40年以來,LGBT同志被病理化、污名化的歷史,以及青少年同志不被看見的處境,對應到近年同志運動興起、保守教會阻擋同志教育的現況,在完整的污名歷史回顧中,作者也以醫師工作的經驗對精神醫療提出反思。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爽歪歪網站轉載。僅向作者致謝。)
一個前醫生的非病人誌
同性戀去病化四十年後

.
作者:吳易叡(香港大學醫學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任精神科醫師、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研究所博士)
.
那年,民權法案制定了將近十年的美國,開始規定精神病院裡工作病患的薪資。那年,一場中東戰爭引起的石油危機,讓恐慌瀰漫了整個西半球開發國家的街巷。精神失序不再是機構中收容人的專屬肖像。那年,精神病患與正常人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平克佛洛伊德在《黑暗面的》專輯裡唱著:「很難解釋為什麼你瘋了,就算你沒有瘋。」
那年,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分類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裡剔除,標幟了美國精神醫學界和公民運動共同改變「科學事實」的一道重要里程碑。
然而七〇年代的台灣對同志而言,並不美好。
退出聯合國後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文化上開啟了鄉土文學論戰,媒體也上開始出現有關同志的本土論述。白先勇《孽子》筆下新公園裡的青春鳥,在媒體報導中其實是「性變態」。 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聯合報《薇薇夫人》專欄討論了剛被逮補的張漢強:
「前天談到的性變態集團,[…]他們曾在新公園遭遇到幾個人一小組,看到單身的男孩,就有人來搭訕。如果一時好奇心,很可能就中了陷阱。再想脫離是很難的,因此『張漢強』的問題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有『斷袖之癖』的男性,也不是新鮮事了,但竟然發展成集團,可以說是形成了社會問題。」「我們的社會迫切地需要心理醫師,不是屬於精神科的,讓心裡有「疙瘩」的人能找專家談談,免得走向不正常發洩的路途,害別人也害自己。」
對同志一頭霧水的台灣社會,一廂情願地把同志的解釋權交付給「心理專家」,但當時的精神醫學界,就算醫生們也是人手一本DSM,對同志也是一知半解。
所謂專家意見,往往只是一家之言。
例如:八〇年代文榮光醫師從美國受訓回國,針對「性議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文榮光和陳珠璋連續三年蒐集台大精神科求診病患被歸類為同性戀「患者」的病歷,觀察「同性戀引起」的各種症狀,推測它們的成因,並寫成了台灣第一例有關同性戀的精神醫學報告。
這篇大量引用金賽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性學報告的論文,把觀察對象區分為「潛伏性同性戀」、「境遇性同性戀」、「女性化完全同性戀」和「高度男性化完全同性戀」。他們既是同性戀,也是求診的精神疾病患者。弔詭的是,雖然研究目的為調查同性戀引起的各種症狀,卻也包含了「同性戀成因」的討論。
五〇年代初期,《金賽性學報告》直接影響、或間接促成了美國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界關於同性戀是疾病與否的辯論。但在台灣似乎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同性戀在已被想當然爾置放在一個生態位階上。
經濟狂飆的年代,以都會為主的基督教福音運動勢如破竹地「復興」。熟悉或領略過這股風氣的台灣人應該對社會學家彭懷真《同性戀、自殺、精神病》這本書不陌生。這本書的寫作目的,當然是藉此希冀一個「理性」、「健康」的社會。寫到同性戀,彭懷真大量引述文榮光對同性戀的描述,也說這本書廣泛徵詢精神醫學界的意見。
同性戀和自殺、精神病一樣,在同一個時期浮現為社會沈重的沈痾,於是一起被框起來談。哲學家Ian Hacking說的,動態的名目論(dynamic nominalism),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雙雙倒臥在一氧化碳中的北一女資優生,加深了人們對社會邊緣「物種」的刻板印象。在被精英升學主義蠱惑的台灣社會,許多人就像北一女校長一樣選擇別過臉去:「我們學校裡沒有同性戀。」
民歌手莊祖宜這樣唱著:「沒有誰認真地替他們說話,沒有誰認真地為他們解答。」直到葉永誌,一個帶有女性氣質的國中少年倒臥在血泊中,被罷凌致死。
被賦予厚望的專家,卻往往是被動的。把專家(expert)拆成兩個字:「X」和「spurt」,意思就是壓力下擠出的未知水滴(unknown drip under pressure)。他們一再被迫對社會案件表態,代表的是他們也只能窺豹一斑的科學真相。
一九九三年,高雄陸軍八○二醫院在一年之內發現十多名同志軍人,並因此辦理停役。那時的台灣軍方認為同性戀會導致愛滋病在軍隊中蔓延。因此國防部規定,只要役男體檢時出具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的證明,並經過軍醫院複檢證明為同性戀者,可以「性心理變態」判為丁等體位而免役。
台灣的精神醫學界開始「認識」同志,實際上是隨著性別人權工作者、同志團體的逐漸現身,和社會氛圍的逐漸開放。醫界、學術界、政府單位和公民代表的持續互動,才讓醫生的被動的參與開始轉化為主動支持。
一九九二年,台北陽明醫院周勵志醫生帶領的同志成長團體是第一樁精神醫學在同志議題上的積極作為。透過醫療人員的引導,同志們每週定期聚會,談生活話題,也談時事。三年後,演變為拓展團體的小北同志社開始到電台、酒吧進行有關同志知識的宣導。
當然,醫界對於同志的態度要整個轉換,還嫌太早。和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活動的美國非異性戀醫護社團比起來,父權的台灣醫界依然無法提供醫護人員結社、發出集體聲明的條件。一直到最近十年,身為同志或支持同志的醫護人員,才開始著手研究照護者的態度分析,檢討異性戀主義、同性戀恐懼對精神醫療產生的傷害。
去年三月,由性別團體、直/同志醫護人員和精神醫學界自主發起的「當我們同在異起」研討會,首度檢討了在台灣,同志與精神醫學半世紀來糾葛的關係。而其實促成這波檢討聲浪的其中一道導火線,竟然是年初,是否要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綱的爭議。
四十年了,同性戀在DSM當中已經不是一個病。但在台灣社會中一直都是。
狂飆的冷戰後期,台灣身為一個國際孤兒,社會快速變遷,新價值不斷衝撞著國家安全的現實條件底下,在訴諸「民族復興」、「救亡圖存」的台灣,以道德、健全社會為訴求的保守勢力,找到了見縫插針的絕佳機會,發揮他們的論述。
以父權異性戀為骨幹的家庭價值正在鞏固,香火不能斷;經濟奇蹟正在發生。從農業到工業,馳速轉型的生產線裡看不見同性戀;福音的疾風烈火要在此地復興,要拯救世道。同性戀怎麼可以不是一種病呢?
反過來看精神醫學,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從大監禁到神經傳導物質理論,它在社會中的功能、操作的方式沒有一刻不在變動。但是在台灣,或同為西方醫學「後進者」的華人世界,它很可能只是知識精英安身的傳統選擇,知識或在一個醫生立業後自此停滯。
但在瞬息萬變的台灣社會,他們面臨的挑戰比歐美更灼熱。除了兼顧專業、中立、客觀性之外,更大的任務是符合市場的需求和服務使用者的觀感。除了醫學新知的更新與傳遞之外,還必須給予逐漸開放的社會某種程度的再保證;他們肩負了對於一個未知領域被迫投予想像、詮釋和解決手段的多重任務。
還泅泳於渾沌裡的科學,語言是彈性的,事實是片斷的。
有時候精神科醫生對大眾解釋「發展過程當中,有些同性、異性之間的親密行為並不是固著的」時候,許多時候很輕易而無奈地被轉述為「同性戀是可以預防的」。「再保證(reassurance)」被要求為「鐵口直斷」;「選擇題」變成了「是非題」。
記得學生時代跟診。進門的大學男生痛苦地對醫生說:「我發現對學長有莫名的好感。」「我好怕自己將來成為流浪漢、罪犯,再不然就是同性戀!」其實,他尋求認同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但醫生對他自己也沒把握的話題,也只能支吾地說:「先別擔心,你可能只是英雄情結的固著而已。」
這男大生已經二十多歲了呀!我好奇,他現在到底在哪裡?但我不敢去想。
因為我更無法忘記八年前,剛成為住院醫生的第二個月,某個晚上接到電話,話筒的遠端聲音如此氣弱卻鎮定,而被告知患憂鬱症的女同好友選擇結束生命時,身為一位新科專業人士的無力感與罪惡。直到如今離開醫學崗位之後,時時耳聞更多身為同志的醫護人員選擇了以更極端的方式離開。他們不只離開醫業,也離開了塵世。他們的離去,在如此固若金湯的結構裡,似乎是一種必然。
我常揶揄地想,希波克拉底誓言裡的「莫傷害」召喚的是誰?如果同性戀一直都沒有除病化那不更好?那將不會有模糊地帶,讓「何謂同志」如此難解的問句在調色盤上任意沾染人所好惡的顏色。那也將不會是一條道德命題,在社會上接受嚴厲的刀剮。在精神機構裡,至少還有溫飽,至少有救命的最後防線。
然而這是虛妄的。時代在前進,精神醫學也在前進。
國界瓦解了,各路同、異、跨性戀人如今可以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姿勢放逐自己、暫時旅居,甚或建立自己的人生。但國家退場之後,市場便開起一連串的佔領計劃。DSM在改版中,這個與藥物開發商關係匪淺的診斷聖經,將如何主宰著我們的精神狀態甚至公民身分?則仍然無人能夠預測。
.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the City Magazine (HowWhy) Issue 437. Feb. 2013
Posted 2nd February by Harry Yi-Jui Wu
文章出處:原刊載於香港號外雜誌2013年2月號「中港台同志運動專輯」
http://crookedtimberlands.blogspot.hk/2013/02/an-ex-doctors-note-on-non-patients-40.html…